- 积分
- 387
游客
- 元宝
- 0 个
- 银子
- 0 两
- 贡献
- 0 点
- 威望
- 0 点
- 注册时间
- 2010-10-26
- 在线时间
- 309 小时
游客

|
注册成为金坛论坛会员,与千万金坛网友开启缘分旅程!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帐号?现在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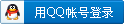
x
驱车深山远,苍翠风林间,
古刹菩提下,去俗不思凡。
是否终老此,徘徊鹭鹚涧,
妻儿翘首望,依依把家还。
二月二,家家带女儿。这是我们茅山老区一年一度的风俗。我一到娘家,父亲就打开电脑,得意的让我看他的新作《去俗难》。
老爸,洪伟,耄耋之年,茅山脚下一老翁,患有严重的心脏病,但他仍健康地活着,他靠的就是乐观、好学,喜欢自娱自乐和追求新鲜事物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老爸的爱好和生活,足足让他的同龄人甚至是中青年自叹不如。
老爸一生坎坷,1957年在常州粮食局工作,反右期间,由于会提意见得罪了领导,被打成“右派”,但看在他年轻,不忍给他戴“帽子”葬送一生,搞了个内定下放回家,可就是没这个“帽子”,后来平反时却害苦了父亲。不甘寂寞的父亲,又和几个朋友闯天下,去了青海,在一个和苏联人合作的大企业工作。仗着在祖父那里学了点“三脚猫”的医术(祖父曾是北阀军军医),穿上白大褂一本正经地充起了厂医,靠着ABC和阿司匹林便成了“洪医生”。不过父亲好学,肯钻研,不久便会看病,还会动些小手术。父亲厂医当得有模有样,他似乎看到了光明和前途,便从老家把母亲和我这个长女接到了青海。然而好景不长,1963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,苏联和我国的关系日趋紧张,最终苏联撤走了所有的专家和技术人员,偌大的工厂顷刻瘫痪,父亲的选择也只好是哪里来哪里去,举家迁回了江苏老家———金坛茅麓。
回家后,不会农田生活的父母拿不足劳力的工分,一年下来,免不了是个“超支户”,粮草都称不回来。那时,买什么都要票,粮票、油票、布票、肥皂票,连火柴都要票,这些全靠爷爷一个月35元的工资来维持。我们一家6口和爷爷、奶奶、小姑、小叔共十口人住在一起,是个大家庭,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。一大锅见不着米的粥是一人三大碗,山芋丝、胡萝卜、南瓜做成的饭是一人两大碗,青菜汤或萝卜汤一大锅,喝的个个肚子涨涨的。我们住老街上,房子也是老房子,下到大雨,家里的脚盆、面盆,碗勺全部拿到各处等漏。父亲总是冒着风雨上房“捉漏”,捉了这里,那里漏。全年的生活是两个字:“苦”和“难”。
这还算太平的,到了文革期间,那日子才不是人过的。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”时,父亲会写,自然成了两派争斗中的“人物”。一次,父亲指点对方大字报下面画的向日葵叶子不圆,说这叶子尖尖的,像国民党党徽。话音未落,“啪啪”对方两个巴掌就打在了父亲的脸上,随即一个“现行反革命”分子产生了。父亲被抓了起来,接着就是抄家,说家里有“国民党党徽”,此时爷爷也被抓了起来,定为“国民党老牌特务”。顷刻,家就不成家了,被抢、被砸,奶奶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气得卧床不起,没多久便离开了人世。父亲和祖父戴着高帽子游行,自己高喊着打到自己。父亲是“老账新账”一起算,高帽子自然是高得不能再高了,一阵大风吹来,父亲首先保护的是自己的高帽子。家里的大字报用绳子拉着,像晒被子一样横竖挂着,我们在家都是弯着腰走路,不能把大字报碰破,否则,倒霉的将是祖父和父亲。他们被各阶层不断地拉出去批斗,腿跪得又红又肿,回来都关在黑房子里,弟妹们胆小,只有我敢去送饭。因为我们是“黑五类”子女,常常遭受到同龄人的唾骂和追打,就这样,我们过着人不人,鬼不鬼的生活。
一声春雷,“四人帮”粉碎了。平反落实政策的春风吹到了全国各地,也吹到了我们山区。祖父平反了,可父亲却因没“帽子”一次次被排除在落实政策之外。父亲心灵受着煎熬,他天天翘首盼望着,心脏病复发了,他强撑着,父亲就不信等不到平反就这样去见马克思。他坚信地对我们说:“平反的春风一定会吹到我,我相信党,相信邓小平。”终于有一天,父亲接到了平反通知,父亲哭了,在那艰难困苦、饱受折磨的日子里,他从没掉过一滴眼泪,可这次父亲的泪水浸透了他的脸庞。春风终于吹到了父亲,阳光真正地照进了我们全家每个人的心里。从此,我们都挺直了腰杆,灿烂的笑容绽放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,沉重的“成分论”、“家庭论”统统地扫进了垃圾箱。
改革开放之后,打开了国门,向世界开放。靠着政策,靠着勤劳致富,父亲盖起了楼房,真正地过起了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。接着,洗衣机、电视机、电冰箱、微波炉、空调等进入了家庭,父亲也由此渐渐的进入了现代化的生活。
父亲爱好音乐,从半导体、立体收音机,录、放机到组合音像、VCD、DVD、电子琴等,更新了一代又一代,家里的磁带和碟片是一抽屉一抽屉的。一次我回娘家,帮父亲收拾床铺,一见床上,惊呆了,这哪里是床?简直是一个“百宝铺”!玩意头可真多,光是大小录音机就是四只,各占一个功能,还有多种遥控器、血压器、报警器。家里报警器到处可见,控制水缸放水的,烧开水的,守大门的,捉老鼠的,羊圈里都安装了报警器,这些报警器可都是父亲发明安装的呢。
父亲紧跟时代脉搏,学会了发信息,接连换了三只手机。当他看到电脑有那么多功能时,一心向往着。一次,父亲悄悄对我说:“我要是有台电脑啊,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,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。”因为说这话时,父亲已经是78岁的高龄了。见到父亲沮丧的神情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,想到父亲这一生很不容易,不要说我们现在有这个经济条件,就是没有,也要满足老人家的心愿。我们姐妹一商量,一致同意,于是一台新电脑出现在了父亲的面前。父亲激动的说不出话,只说:“好了,好了,今后我什么也不需要了。”父亲虚心好学,逮到一个懂电脑的就拜以为师。一年时间,父亲便学会了上网聊天,写博客,收发邮件,网上购物,打字还都是盲打。他经常和人聊天聊地,各种新闻无所不知,别人惊讶的问他:“你一个山里的老头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啊?”父亲总是漫不经心的说:“我上网看到的。”而对方却吃惊的睁大了双眼,或许在暗暗地想:“你在吹牛吧?”
总以为父亲有了电脑后会对别的不感兴趣了,谁知,没过多久,父亲又悄悄问我:“数码相机好不好啊?”我说:“当然好啊,您想要吗?”“不、不、不,我只是随便问问。”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回答着。父亲是个摄影爱好者,到哪里都不忘带着他那个用了十多年的傻瓜照相机。田园里劳作的农民、小草小花、小猫小狗都曾是他镜头下的景物,他拍的就是一个乐趣。可父亲都八十了,再买数码相机有这个必要吗?我试探着和母亲说了一下,母亲立即反对:“不行,你什么都依他,他要上天,你还搭梯子不成?”我知道,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人,她和父亲的消费观念截然不同,每次家里置办一件东西,母亲总是反对,甚至有时一直吵到自己尝到甜头才会默认或表扬父亲。就像电脑,直到自己也在上面学会了打游戏,才不跟父亲计较。由于母亲的这次坚决反对,我也就不提了,可是,每次回家见父亲在玩弄旧相机时,想起父亲那渴望的眼神,就像是有根刺扎在我心里。一天,我打电话叫父亲上城里来玩,我对父亲说:“走,陪你看数码相机去。”父亲眼睛一亮:“真的?”那兴奋样就像一个小孩,“太好了,太好了。”买回了数码相机,我问父亲:“今后还需要什么吗?”父亲毫不犹豫地说:“真的什么也不需要了,满足了,满足了。”我打电话回去告诉母亲,数码相机买了,不要说父亲,父亲一气心脏病会复发的,母亲答应了。父亲带着数码相机像揣着个大元宝似的,高高兴兴地回了家,他打来电话告诉我,和母亲生活快60年了,第一次买东西没反对,还说买得好,说母亲在和谐社会也变得和谐了,他感到非常幸福。
一日,在家里见父亲在擦那被撞过多次的小电瓶车,我不由地说道:“老爸,现在有一种新型的自动充电的电瓶车,上金坛来回不要充电。”母亲立即朝我使了个眼色,我“啊”的一下,捂住嘴,自知说漏了嘴,但愿父亲没往心里去。谁知父亲却搭腔道:“我在网上看到了这种车,其实我心里早就想了。”天啦,这可不是闹着玩的,那车速比这旧的快多了,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,那可不得了。有一天中午,父亲推着破电动车,上面还有一捆青菜出现在我家门口,他满头大汗,气喘吁吁,我吓了一跳。父亲说本来老早就能到的,可是骑到半路电动车没电了,一直推到城里的。一斤青菜值几个钱,把个老父亲折腾成这样!我说:“你不好把青菜扔了推还轻点。”父亲说:“就是送青菜给你的。”我的心痛了,青菜和父亲的身体相比,孰轻孰重?可是父亲宁可自己受累也不舍弃那捆青菜,使我深深感受到那种比山重,比海深的父爱。吃饭时父亲对我说:“说真心话,我最怕你母亲说我‘一大把年纪了能过几年,还要追新潮,赶时髦’,其实,我觉得自己很年轻呢!”小孩生下来会吃奶是天性,老人怕老大概也是天性。八十好几了,人家问:“多大啦?”回答总是说:“小啰。”这,就是对生命的一种执着。父亲也不例外,他思维敏捷,行动利索不亚于中年人,但我想,假如父亲推车时因体力不支心脏病复发,那后果不堪设想,特别是在父亲的晚年,我不能让他有一点遗憾。于是,一个决定下了,给父亲买车!
父亲开心地站在新车前,让女儿给他左右拍照。父亲说:“这下,我真的心满意足了,再不需要什么了。”我也这样想:老爸,你还需要什么呢?
父亲白天骑着车子,带着数码相机,来回于城乡或穿越在山水之间,晚上把照片发到电脑上和母亲一起欣赏,共享着人生的快乐。父亲说:“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幸福生活,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啊。”母亲也来个幽默:“老头子,你还需要什么,我拿养老钱给你买。”父亲激动说:“谢谢,谢谢,真的什么也不需要了。”
可是,我这次回娘家临走时,父亲又笑着向我走来,我感觉不妙:老爸,该不是嫌电瓶车车速比不上汽车,要买汽车吧?父亲腼腆地用嘴抿了几下问我:“参加书法协会有什么条件啊,我想参加。”我恍然大悟,难怪最近父亲一有空就上楼练书法,难怪父亲上次来城里要去参观书法展览,原来父亲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,也许这就是生命力。
老爸,我服你了,你真是一位年轻的老爸!
作者:洪丽霞
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