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积分
- 179
游客
- 元宝
- 0 个
- 银子
- -12 两
- 贡献
- -12 点
- 威望
- 0 点
- 注册时间
- 2010-10-26
- 在线时间
- 122 小时
游客
|
注册成为金坛论坛会员,与千万金坛网友开启缘分旅程!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帐号?现在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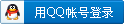
x
有生以来,我就买过一条游泳裤,而且,是在物质最匮乏,生活最贫困的学生时代买的。这条游泳裤,陪伴了我大半辈子。穿着它,我学会了游泳;穿着它,我陪伴我的两个儿子学会了游泳。在40多年前的乡村,一个普通的青年,能够穿一条游泳裤游泳,那确实是很时尚、很时髦、很引领潮流的。每每想起这条游泳裤,就情不自禁地让我想起两件刻骨铭心的事情。
毛泽东主席是一位游泳爱好者,他曾多次畅游长江,并写下著名诗词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:“才饮长沙水,又食武昌鱼。万里长江横渡,极目楚天舒。不管风吹浪打,胜似闲庭信步,今日得宽余,子在川上曰:逝者如斯夫……”诗词极具豪情。1966年7月16日,毛泽东最后一次横渡长江之后,“7·16”也被确定为毛泽东畅游长江纪念日。8月17日,毛泽东在《人民日报》社论《在游泳中学会游泳》中指出:“一切革命者,一切革命青年,都应该经风雨,见世面。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中成长,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。”他还说:“游泳是同大自然做斗争的一种运动。”想当年,毛主席的这个最高指示一发出来,举国上下就沸腾起来了,由此,在全国掀起了一股“全民游泳”的热潮,游泳就这样与政治紧紧挂上了钩。在那个特定时期,游泳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健身运动,而是上升到了表决心、表立场的政治高度。
就在那股声势浩大的热潮中,我也一反常态,融入到浩浩荡荡的游泳大军中。为了学会游泳,我花了近两天的伙食费,买了一条墨绿色的粗布游泳裤。当年,由于学习游泳的场所在练湖,离我读书的学校有三、四里路,再加上人数多,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之后,我们学校就整队出发了,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,迈着整齐的步伐,穿过老西门大街。穿过林荫大道,就来到了闪银耀金的泱泱练湖。一刹那工夫,湖面上就像漂了无数的彩球,成百上千号人像水中蛟龙,在水里“兴风作浪”,练湖还真成了《三国》里“练兵的湖”,成了无数少男少女们欢乐的海洋了。在练湖,我先后学习了两个多星期,初步掌握了游泳的要领,在湖边我也会蹬两脚了。尽管,我的姿势不美,正宗的“狗爬式”,尽管距离不远,头二十米的样子,但毕竟不算是“门外汉”了,我引以为豪。
其实,在江南水乡,河沟交错,湖塘密布,到处都是天然的免费浴场,在青少年,尤其是男性中,不会游泳的“旱鸭子”、“铁秤砣”寥寥无几。要么,就是“惯宝宝”,是家长把他们“顶在头顶上怕摔下来,含在嘴里怕咽下去”的那种,家长管得严,整个夏天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。然而,我早先也是“旱鸭子”、“铁秤砣”,但我却不属于这两种人。
我不是胆小如鼠的人。小时候,我在邻县小镇上应该说是名闻遐迩的“风云人物”,人称“孙猴子”。一是我长得瘦小、一身排骨。村上的老人们都说我是“吃米心,长鬼精”的家伙;二是我顽皮。虽然,我在学校里读书不用大人们操心,但到了节假日,街头巷尾、田间阡陌就成了我“大闹天宫”的世界了。划连叉,笃一字,常常玩转一条街,有两次把新做的裤子都笃破了。有时候,一放学,我就背着书包径直来到住在后街的同学家门口的晒场上,找两张“骨排凳”,一根长竹竿和几块“八五”砖,一副跳高架子的材料就备齐了。然后,把长竹竿架在两张相距不远的凳子上,几个小玩伴就像从笼子里放飞的小鸟,在场上又蹦又跳,欢呼雀跃。说来也怪,过去我们那样肆无忌惮地在外面疯玩,还从来未有一个人把身上弄得伤筋挫骨。或许,那时候的小孩没有现在的金贵和娇养吧。除了这些,我还常在十字街口、四桥背上舞金箍棒、顶鸡毛帚,在骄阳似火的三伏天,一个人在篮球场运球、投球,以致被撑伞戴帽的路人骂作“不要命”、“没得魂”。更不要命、没得魂的,是在大跃进年代的一天下午,我在家把玩父亲单位上发给他“除四害”用的野鸡枪,一不小心走了火,“砰”一声,把家里的门打了一个洞。
在家里,我排行老大,不是父母特别娇惯、看管的人。我上面曾有一个姐姐,生下不久就夭折了,按理说父母是应该十分宠爱我的。但是,我的父母没有这样,尤其是我的父亲,他从来不把对孩子的爱写在脸上,讲在嘴上,也从不强行要求我这样做,那样做,一切顺其自然。所以,除了管吃、管穿、管做人规矩,父母一般不过问其他的事。从小,我们就很自由、宽松,除非我为了玩惹了祸,譬如说把短裤撕豁了,玩野鸡枪走火了等等。
然而,我为什么到20岁那年才学会游泳呢?这就是我要说的关于游泳的第二件事了。
我记得那时候自己大概读小学三年级,五、六月份的光景,天气已经很热了。每天放学,我趁到街外割兔草的机会,总与几个玩伴到大塘里洗冷水澡。由于刚刚学游泳,我都是在塘边上扑腾。学了两天,玩伴开始用一只手托住我的下巴向前划水,划了几步,玩伴一脱手,着实让我喝了几口水,鼻子里呛得几乎要冒烟。好在那时候大塘里的水碧汪清澄,玩伴们跟我说学游泳都是这样的,喝几次水就会了。正当我对游泳兴趣盎然的时候,突然有一天发生了变故。
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,我的班主任王仪凤老师到我家隔壁青货行(那时小镇没有菜市场)的肉墩头上买肉。当时,我刚从家里出来准备出去玩,被她看见了,一下子喊住了我。她问我:“昨天放学之后,你做什么的啊?”我脱口而出:“割兔草啊。”“还做什么的?”我不知道王老师还要追问一句,心里想,不好了,恐怕洗冷水澡的事有人告发了,我不敢再瞒了,吞吞吐吐地说“我……我……洗冷水澡了。”“多少人洗的?”“多了,都不是我们班上的。”“那么,这样做好吗?”“不好。”“那你以后还这样吗?”王老师一连串的反问句,让我猝不及防,不得不老实认错:“不了,以后再也不了。”“好,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。”就这样,从那以后的九年时间里,我再也没有敢背着老师去下过一次水,学习游泳。
那时候的老师,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是皇上;那时候老师讲的话,在我稚嫩的脑子里就是圣旨。之后,我也从事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。但是,从“马列主义的第一张大字报”,到黄帅造老师的反,到张铁生交白卷,中国两千年的传统教育思想,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教育思想,都被全盘否定了,都被当作大毒草连根铲除了,“怀疑一切,打倒一切”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,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式。然而,“拆屋一顿饭,建房三担米”,毁掉的东西,以后再想重新建立起来,就不是一朝一夕、一蹴而就的事了。
好在十年梦魇的历史已经结束了,戴在老师头上的“臭老九”的帽子终于被摘除了,教育战线又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,尊师重教渐成风气,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日益提升。
如今,当我饶有兴致地回想起当年学习游泳的事情时,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王仪凤老师。王仪凤老师说话虽然不是那么和蔼可亲,但她没有骂我一句,没有打我一下,完全是从安全角度为我考虑,让我一度做了“旱鸭子”、“铁秤砣”,我也没有一句怨言和半丝忌恨。因为,我知道她的用意和初衷。看到现在每逢暑假,许多小孩偷偷下河游泳溺亡的新闻,我实在庆幸自己曾经遇到了一位负责任的老师。
作者:黄生龙金沙周刊
|
|